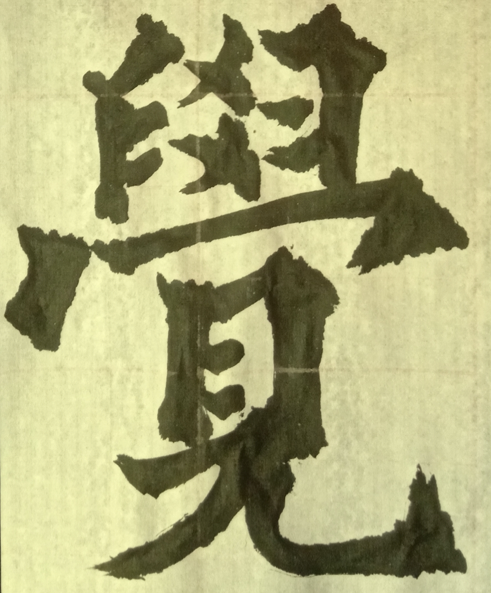翻譯動機
本篇論文同樣由麥卡洛醫生領銜撰寫,發表於2020年12月30日,較諸筆者之前翻譯的《新冠肺炎早期門診治療的病理生理學基本原理》內容多有更新,論述也更完整,因此值得再花筆墨重譯成中文。麥卡洛醫生這篇論文是寫給英文世界的醫界、公衛政策制定者看的,而本篇《 新冠肺炎多元藥物早期治療 》所預設的讀者則上至中文世界的廟堂精英,下至市井平民,筆者尤其希望普通人也能獲得這些資訊,因為人在未知之中便不免焦慮,而若人們對事相能多一份瞭解,就能少一份隨波逐流。智慧便生於是,全身葆真亦在於是。
論文原文:《Multifaceted highly targeted sequential multidrug treatment of early ambulatory high-risk SARS-CoV-2 infection (COVID-19)》,筆者譯為《針對高風險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全方位高標靶梯次性多元藥物早期非臥床治療法》
論文前言
現代醫學防治瘟疫的方法共有四根支柱:
- 控制接觸傳染
- 早期治療
- 住院治療
- 疫苗
- (預防性療法)
上述支柱重點針對的項目各有不同。控制接觸傳染目的是阻止病毒傳播。早期治療目的是讓患者在染疫初期可以在家接受治療,避免症狀惡化,從而降低住院率、死亡率。住院治療目的是搶救處於染疫末期的重症患者,是避免患者死亡的最後一重保險。疫苗的目的是群體免疫。以上即現代醫學的防疫四支柱。預防性療法在必要時可以當成第五根支柱,其目的是避免疫情擴散和降低染病後發展成重症的機率。
許多國家目前的防疫策略大多著重於1、3、4這三根支柱。在那些新冠無藥可治的觀念盛行的國家裡,現代醫學的防疫大廈便缺了早期治療這根支柱,造成染疫者不得不坐等症狀惡化才能送院,接受遲來的醫療照護。大多數緊急送醫的新冠病患一開始並不需要接受插管、呼吸器治療,但若症狀惡化到需要輸氧,死亡率便會上升到12%。在所有送醫治療的新冠病患中,有1/4會惡化到需要呼吸器、進階循環輔助、洗腎治療,這1/4的群體死亡率超過了25%。根據麥卡洛醫生等人觀察,在患者染疫初期,症狀猶輕之時,透過遠端診療的方式讓病患在家予以早期治療,便能避免大部分的住院案例發生。
大多數可能致命的病毒感染都需要使用多元藥物予以早期治療。由於新冠肺炎染疫初期至末期依次會出現「病毒大量複製」、「免疫風暴導致的器官受損、功能失常」、「血管內皮受損導致血小板聚集,引發血栓」三個階段,單用一種藥物治療新冠便有些不切實際。但至今為止,醫界尚未生成針對非臥床病患的口服藥物療法臨床實驗報告,短期內也可能不會出現。大多數現有的口服藥物療法臨床實驗或者規模太小,或者效力不足,或未導入遮盲的實驗方法,或被打壓,總之並未產生決定性的結論。在這些前提下,新冠肺炎的病理生理學、接受治療的自然史組[1](treated natural history group)的狀況、以及醫師的臨床判斷等便須被綜合起來,作為當前新冠肺炎非臥床病患的風險分層管理方法的指引,而目前的觀察性研究報告也有足夠證據,證明早期治療方案所使用的平價、安全而普遍流通的藥物既安全又有效。
新冠肺炎患者的風險分層管理方案於焉產生。大多數50歲以下且無任何慢性病史,健康情況良好的人在染疫後會出現有限的身體不適,若無出現任何嚴重症狀,便不須予以特殊治療,但若下呼吸道的症狀加劇,便需評估血氧濃度,照肺部X光,觀察是否有充血或肺浸潤的症狀。50歲以上,或者50歲以下但患有至少一項共病症[2]的患者染疫後,住院風險上升之外,死亡率也會超過1%。患有更多慢性疾病(肥胖、糖尿病、心臟病、肺功能失常、腎病、惡性腫瘤)的高齡人口,染疫死亡率可能高達40%,這就導致早期治療對這個群體來說很有必要。新冠肺炎就像其他病毒感染所引發的疾病,同樣的藥,越早使用,效果越好;拖延到病情惡化住院了才使用,效果越差。
確診新冠後,以下三條治療原則可用來治療非臥床病患:
- 組合運用抗病毒藥物⟶目的是抑制病毒複製(立即使用)。
- 使用皮質類固醇⟶目的是緩和免疫風暴(呼吸道症狀加劇時)。
- 抗血小板/抗凝血療法⟶目的是預防和控制微型、大型血栓(疑似有血栓症狀時)。
尚未取得篩檢結果,或者篩檢結果為陰性,但有出現發燒、病毒感染造成的身體不適、鼻塞、失去味覺、嗅覺、乾咳等新冠肺炎典型症狀的人,以上三條治療原則也可參照運用。
以下開始介紹具體治療方法。
降低病毒傳播率
隔離的主要目的是控制病毒傳播範圍。目前世界各國防疫政策強調要在公共場合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然而許多研究顯示,病毒最主要的傳播場所是私宅。因此,本論文建議,當家中有人確診,其他未染疫者便需戴口罩、勤洗手,也需要常常消毒桌檯、門把、電話話筒、以及其他常用物品。若條件允許,可暫居他處。許多研究顯示,目前的公共場合防疫政策效果有限,因此把這些政策延伸到最常發生病毒傳播的私宅之中是合理考量。
以上建議最好能與早期治療配合施行。染疫者在家接受早期治療,其中一個好處是可以使用遠端診療、快遞藥物等方式,讓染疫者在家安坐,不需病急出外投醫,降低病毒傳播率之外,也可以減少病人因為症狀惡化而住院的機率。反之,若抱持新冠無藥可治的觀念,一線醫護不免惶恐,病人也不免有無助、被拋棄感,因此出現不願隔離等死,選擇急診就醫的現象。這除了會增加病毒傳播率,也會加重醫護負擔,病人的住院率、死亡率也會大大攀升。
確診者居家隔離期間應注意通風。由於病人呼出的空氣被預期會夾帶病毒顆粒,而病毒顆粒會存在於氣溶膠中,因此病人在封閉空間一呼一吸,理論上就如同病毒一再感染鼻咽、呼吸道。若能透過開窗、開電扇等方法保持通風,便可降低病人接觸病毒的機率,也或可降低症狀嚴重度,降低居家傳播的機率。另外一種方法則是長時間待在杳無人煙的戶外,不戴口罩,呼吸低病毒濃度的新鮮空氣。
新冠肺炎多元藥物早期治療(一):營養品補充劑輔助療法
新冠爆發以來,學界的一部份注意,放在營養品補充劑在治療和預防新冠上能扮演何種角色。本質上,這些營養品補充劑沒有治病的直接效果。營養品輔助療法的原則有二,首先是觀察染疫死亡和缺乏哪些營養素相關,就針對性地補充那些營養品,其二則是補充那些可以協助修復受損組織、降低病毒複製速度的營養品,從而起到輔助正規治療手段的作用。
鋅
成人普遍缺鋅,而鋅是種強力的病毒複製抑制劑。鋅與羥氯喹是種可以抑制病毒複製的潛在組合,因為羥氯喹是鋅的離子載體,可以協助鋅穿過細胞的脂質細胞膜,進入胞內,從而抑制病毒在人體細胞內的複製。這種安全性很高的療法可於新冠症狀甫出現之際迅速投用。
建議劑量:每天口服220毫克的硫酸鋅(等同於50毫克的鋅。)
維他命D
缺乏維他命D和新冠死亡率上升有相關性,不過缺D通常和高齡、肥胖、糖尿病、膚色暗沈、體適能不佳等因素混在一起,作為一個集群影響染疫死亡率。一個小型的隨機臨床實驗顯示,補充維他命D3可以降低新冠病患的死亡率。
建議劑量:每天補充5000IU的維他命D3。
維他命C
醫界治療許多種病毒感染時都會用上維他命C。治療新冠肺炎時,就可結合使用維他命C與其他營養品補充劑。在本篇論文寫作之際,多項研究口服、靜脈注射補充維他命C的隨機臨床試驗正在鋪展。
建議劑量:口服3000毫克維他命C,每日一次。
槲皮素
槲皮素是一種多酚類,在理論上具有降低新冠病毒透過人體細胞表面ACE2[3]侵入細胞的的活性的機制,以及作為鋅的離子載體抑制病毒的蛋白酶[4],還有緩和白細胞介素-6[5]引起的發炎反應等功能。這些作用機制在抑制病毒複製、緩和免疫反應等層面可產生正面影響。因此若能結合其他營養品補充劑使用,應可在染疫初期,起到降低病毒複製和組織細胞受損的輔助性作用。
建議劑量:口服500毫克槲皮素,一天兩次。
點評
對普通人來說,〈營養品補充劑〉這個小節可能是本文最有價值的段落,因為鋅、維他命這些營養品安全、平價,並且從藥理來說可用於治療新冠肺炎以外的病毒感染,比如一般小感冒。至於槲皮素,槲皮素廣泛存在於自然界中,各種漿果、茶葉、蘋果、洋蔥、番茄、花椰菜等等皆有之。根據《A role for quercetin in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這篇論文的摘要,槲皮素在藥理上有抑制病毒複製的作用,在臨床實驗上則顯示有抗發炎和抑制血栓的作用。維基百科則引述2005、2007年共三篇論文,提到實驗室體外細胞研究顯示檞皮素可能轉變為致癌物,是否對人、動物產生致癌效果則未知,維基百科也提到槲皮素可能和抗菌劑氟喹諾酮產生衝突,不過這些都是10年前的資訊了,筆者建議有心人可自行研究。為保險起見,可在有症狀時才服用槲皮素,暫且不要把槲皮素補充劑當作維他命天天服用,日常盡量從天然食材攝取,這或許會是比較理性的選擇。而因為槲皮素與羥氯喹同樣是鋅的離子載體,當羥氯喹無法取得時,槲皮素會是種有效的替代品。或許有朝一日,鋅+維他命D3+維他命C+槲皮素會成為普通感冒的全民解方。
新冠肺炎多元藥物早期治療(二):可在人體細胞內起作用的抗感染療法
減少病毒在人體內複製的速度、數量、持續時間,是新冠症狀出現的第一天就開始使用抗病毒療法的目的。早期治療的目的是盡可能減輕病毒對呼吸道表皮、血管內皮、人體器官所造成的傷害。具體來說,早期治療可以減輕新冠病毒在宿主體內增生所引起的種種不良反應,包括發炎反應,免疫風暴、血管內皮受損、血栓等等。新冠重症率、死亡率的上升,和患者年齡是否超過50歲、是否具有共病症有關,因此治療這個群體時,醫師需要「標籤外」[6]開立至少兩種在臨床上、藥理上有必要,並且有在市場上流通的抗感染藥物。反之,若不開立口服抗感染藥物,醫師須與病人取得共識,並且必須告知病患,新冠肺炎的自然史顯示,高風險病患在沒有接受治療的情況下,將面臨住院、在住院時產生併發症,死亡的風險。醫病雙方需要理解,唯一可能避免住院的方法,是憑經驗使用安全性和有效性有一定水準的「梯次性多元藥物療法」(sequential multidrug therapy, 簡稱SMDT)。近來新冠病患則多出了靜脈注射單株抗體這種治療方案,但因不是所有病患都能取得單株抗體,供給端也無法盡數滿足需求端,所以開立口服抗感染藥物仍有存在的必要性。
羥氯喹
羥氯喹是種可以讓病毒粒子胞內體[7]傳輸功能受損的抗瘧疾/抗發炎藥物。羥氯喹也是鋅的離子載體,可以把鋅運進細胞內,阻斷新冠病毒複製時所依賴的RNA聚合酶,從而防止病毒複製。目前持續更新的羥氯喹綜合研究顯示:
- 在所有於染疫晚期(發展成重症而住院)才投用羥氯喹治療新冠的研究中,63%顯示使用羥氯喹有益。
- 在所有使用羥氯喹進行早期治療的研究中,100%顯示有益,並且症狀發展成重症、住院、死亡的相關風險降低了64%。
目前有關羥氯喹的小型隨機臨床實驗不足以得出決定性的結論,理由如下:
- 沒有使用安慰劑的控制組
- 不是遮盲實驗
- 判斷藥物實驗結果是否有益的主要考量點更易。比如有些臨床實驗評估療法是否有效的主要考量點為是否死亡,有些為是否住院⋯⋯。
- 由沒有盲測的醫療人員決定考量點(比如是否需要輸氧)。
- 臨床實驗樣本規模太小,或者在管理層面上遭到終止。
- 臨床實驗結合使用了其他抗病毒藥物
美國FDA 1955年便批准羥氯喹這種藥物,至今全世界有上千萬人使用過羥氯喹,許多國家的藥房都有販售,羥氯喹的安全性也為人熟知。服用羥氯喹後,有<1%的人會產生無症狀的心律QT間期延長的現象。那些患有「葡萄糖-六-磷酸鹽脫氫脢缺乏症」(蠶豆症)[8]的人不應服用羥氯喹。感染新冠肺炎並且發展成重症的病患,在不服用羥氯喹的情況下,可能發展出有症狀的心律不整,此時的心律不整被歸因於免疫風暴和染病後產生的極度身體不適。藥物監管機構至今並未基於羥氯喹的臨床實驗數據,而宣告服用羥氯喹有安全疑慮。不過少數有QT間期延長病史、家族病史的人,或者有在服用會使QT間期延長的心律調節藥物者,皆須謹慎使用羥氯喹,並且在非臥床的情況下必須監控心臟的QT間期。
典型的羥氯喹使用劑量為200毫克,每日兩次,療程依病情為5天到30天不等。有關羥氯喹的最新資訊,詳參筆者翻譯的《羥氯喹-新冠早期治療的關鍵藥物》。
伊維菌素
伊維菌素是種廣譜抗寄生蟲藥物,對許多病毒皆具抗病毒效力,包括新冠病毒。伊維菌素的藥物耐受性良好[9],治療指數高[10],其安全在性在超過37億次藥物治療案例中得到驗證,在此次新冠肺炎的前期的臨床實驗中,伊維菌素已被單獨開立,或者和多西環素、阿奇黴素結合運用,治療染疫患者。在本論文寫作之際,有數個隨機、前瞻性研究顯示在臨床上使用伊維菌素可以有效治療新冠肺炎。因此,在病人無法使用羥氯喹、無法取得法匹拉韋的情況下,開立單劑口服伊維菌素(劑量200-600mcg/kg,等於6-36毫克,每日一次或隔日一次,總共給藥2-3回)當作「梯次性多元藥物療法」的基底,以在染病初期降低病毒複製速度是合理的選擇。然而,在本篇論文寫作之際,伊維菌素的理想劑量和療程仍有不確定性。在名為「ICON」的研究中,使用伊維菌素和確診患者死亡風險下降48%具有相關性。目前已有36項單獨使用伊維菌素,或與其他藥物結合使用,用以治療非臥床或住院病患的隨機臨床實驗正在進行中。
法匹拉韋
法匹拉韋是種「RNA依賴性RNA聚合酶」[11]的口服選擇性抑制劑[12],並且被多國核准治療新冠肺炎非臥床病患。法匹拉韋很安全,並且在大多數研究中顯示可以把病毒粒子可能從鼻腔脫落的時間縮短到七天。法匹拉韋在療程第一天開立的劑量可以是口服1600-1800毫克,每日兩次,在後續14天的劑量則可為600-800毫克,每日口服兩次,各國所規定的劑量未必相同。在本篇論文寫作之際,多個大型非臥床病患的臨床實驗正在進行中,但可能無法在疫情危機當口即時產生結果。
可以在細胞內產生抗感染作用的抗生素
阿奇黴素
阿奇黴素是一種常用的巨環類抗生素,其抗病毒能力主要來自降低病毒粒子的胞內體傳輸能力,及其抗發炎效果。法國的研究報告表明,相較於未接受治療的群體,服用阿奇黴素和羥氯喹這個藥物組合,和病毒脫落週期縮短、住院率、死亡率降低具相關性。在一項涉及2451名住院病患的大型觀察性研究中,單獨接受阿奇黴素治療的群組的統計數據為:
風險比率(Hazard Ratio)[13]=1.05,95%信賴區間為0.68-1.62,P[14]=0.83。(這個數據意味著單獨服用阿奇黴素反而稍微增加死亡率(HR值),但阿奇黴素療法和死亡率的增加無顯著關係(P值)。)
羥氯喹+阿奇黴素的組合療法在美國以外已被考慮用來當作治療超過30萬具有多種共病症的年長者的標準療法[15]。
阿奇黴素如同羥氯喹,有<1%的病患會產生心律QT間期延長的現象,不過結合兩者治療新冠已顯示具有安全性。阿奇黴素的合理劑量是250毫克,每日口服兩次,依據症狀的持續性或是否發生細菌導致的重複感染(Superinfection),療程從5天到30天不等。
多西環素
多西環素是另一種常見的抗生素,其藥力可以在人體細胞內產生效果,從而降低病毒複製,減輕細胞受損和發炎因子的展現。多西環素的臨床使用劑量濃度在體外實驗中顯示可以對抗新冠病毒,可以在病毒侵入非洲綠猴腎細胞系「Vero E6」細胞後發揮作用(上文許多藥物的治療原理都是從阻斷病毒的胞內體運輸,也就是在病毒未侵入細胞時著手,多西環素則是從病毒侵入細胞後著手治療。)實驗也顯示,多西環素在肺裡的濃度是血漿的兩倍,當在病毒感染初期使用多西環素+伊維菌素的組合,似乎可以達成再染疫10天以內幾近根除新冠病毒的加乘效果。多西環素不會產生心臟方面的副作用,缺點是會引發腸胃不適和導致食道發炎。多西環素和阿奇黴素都有額外防護細菌在上呼吸道引發的重複感染和非典型感染的效果。
多西環素建議劑量為200毫克,接著降成100毫克,每日口服兩次,依症狀持續程度或者是否產生細菌重複感染,療程間期從5天到30天不等。
抗體療法
Bamlanivimab是不久前研發出可以對抗冠狀病毒的單株抗體,並且已經獲准用於治療新冠肺炎的非臥床病患。在「BLAZE-1」隨機臨床實驗中,評估療法有效性的次要考量點為住院率,而接受Bamlanivimab治療的136名受試者中,有4人的症狀發展成重症住院;在沒有接受Bamlanivimab治療的安慰劑組,69人中有7人住院。雖然上述臨床實驗結果不夠堅實,也不足以產生確定性的結論,但基於疫情緊迫的緣由,藥管機構對Bamlanivimab核發了緊急使用許可,用以治療12歲以上、體重至少40公斤,並且有高風險發展成重症住院的病患。目前核准的Bamlanivimab靜脈注射劑量為單劑700毫克,並應在產生新冠症狀10天以內,於確診後儘速使用。靜脈注射的持續時間應超過一個小時,並且在注射完成後需要另外監控病患是否對藥物產生反應,為時同為一個小時(預期病患會對藥物發生反應的機率<5%)。
Casirivimab+Imdevimab是另一種獲得緊急使用許可的抗體療法,適用人群如同Bamlanivimab。Casirivimab和Imdevimab會和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不同區域結合。使用劑量為Casirivimab和Imdevimab各1200毫克,混合在同一劑靜脈注射溶液中,注射時間至少1個小時,並且注射完後需要監控病患情況另一個小時。在二期臨床實驗中,評估療法有效性的次要考量點為住院率,而接受Casirivimab+Imdevimab治療的434人中,有8人的症狀發展成重症住院;接受安慰劑的231人中則有10人住院。不過上述數據仍須謹慎解讀,不足以產生決定性的結論。不過就像本篇論文臚述的許多療法,抗體療法可以被第一線醫療人員納入治療新冠的創發性梯次性多元藥物療法。
若病患是在具備混製抗體注射溶液能力的醫療機構中確診新冠,那麼使用抗體療法是種合理的選擇。相反地,若這種抗體療法可以在病患居家中安全配置,那麼醫師便可給與隔離期間的病患使用抗體療法,以便增強口服藥物療法的效力,因為讓病患在隔離期中外出就醫,取得抗體療法的靜脈注射液並非上策。
點評
與筆者譯介的《新冠肺炎早期治療—全球首篇探討此議題的論文》相較,本篇論文在〈抗感染療法〉的小節新增了伊維菌素、抗體療法的資訊。媒體常以「目前沒有證據證明有效」之類的詞組報導伊維菌素,因而使人產生「伊維菌素在治療新冠上無效」的印象。據麥卡洛醫生今年五月的訪談,羥氯喹在染疫後期才投用,效果有限,伊維菌素則從染疫初期到後期皆具療效,且不像羥氯喹有影響心律的副作用。從本篇論文透露的資訊來說,伊維菌素的問題在於劑量、療程尚未確定,以及實驗並未導入隨機雙盲的實驗方法。就此而言,伊維菌素的確沒有隨機雙盲的臨床實驗證據證明其療效,但這是否代表伊維菌素真的無效?媒體像支筆,寫出什麼要看隱而未現的秉筆者是誰。本篇論文發表將近一年以後,據聞伊維菌素已被美國政府列為其中一種可以治療新冠的藥物(連結在此),殊為可喜。
去年我在月薪只有一萬多塊的某月捐了過半薪水支持我所認為的真理,一年以後,我發現以往所支持的人中似乎有些撕下了偽裝,想起媒體界的一位長官告訴我要懂得保護自己。我所以為的大是大非,未必是真的是非,必須更謹慎求真,這是我選擇翻譯早期治療相關材料的原因,因為我希望有緣來此的讀者能有管道驗證我所呈現的資訊。
新冠肺炎多元藥物早期治療(三): 免疫調節藥物
皮質類固醇
新冠肺炎會引發重症住院,進而導致多重器官衰竭,被歸因於免疫風暴。新冠重症患者的典型症狀包含白血球增多症以及嗜中性白血球低下症,這些患者血清中的白細胞介素-6、白細胞介素-10[16]的含量比正常人高。感染新冠的人首先出現的呼吸道症狀是咳嗽和呼吸困難,而這些症狀可以歸因於發炎和細胞激素的啟動,因此就像治療其他肺部發炎引起的肺功能失調,使用口服皮質類固醇治療產生上述症狀的新冠患者是種合理的藥物干涉。因此,讓患者每四小時使用噴霧劑吸入布地奈德1mg/2ml,或200mcg/吸入劑的療法可以加以運用,不過目前並沒有公開刊登的研究報告證實布地奈德治療新冠的效力。在涉及6425名住院新冠患者的「Recovery」開放式隨機臨床實驗中,有1/3的受試者接受地塞米松治療,另外2/3則接受常規治療,劑量為口服或靜脈注射6毫克地塞米松,每日一次,療程持續時間可高達10天,而實驗發現地塞米松可以降低新冠患者死亡率,數據為:風險比率(Hazard Ratio)=0.65,95%信賴區間為0.51-0.82,P<0.001。另一份整合多份研究結果的分析也與上述數據一致,1703名新冠重症患者中,使用地塞米松可以讓死亡風險相對降低36%。類固醇療法的安全疑慮是可能延長病毒複製的持續時間,不過目前並未被證實。上述臨床研究結果的延伸應用,是給非住院新冠病患在確診第五天以後,或者在產生更嚴重的肺部症狀時,開立類固醇。地塞米松的建議劑量為6毫克,每日口服一次。布地奈德則為1mg/kg,每日口服一次,療程持續5天,依隨療程進展可選擇要維持或降低劑量。
秋水仙鹼
秋水仙鹼是種用於治療痛風和心包炎的非類固醇抗有絲分裂藥物,原理是透過與細胞微管末端結合,防止微管聚集,從而阻擋發炎細胞進入細胞分裂中期。「GRECCO-19」的開放式隨機臨床實驗涉及105名住院新冠病患(其中接受羥氯喹+阿奇黴素治療的有98名,佔全部人數93%),而實驗發現使用秋水仙鹼,與降低患者血液中的D-dimer[17]、臨床症狀的改善有關。依照WHO公布的新冠症狀嚴重度量表(Ordinal Scale for Clinical Improvement)[18],本次實驗中沒有接受秋水仙鹼治療的控制組則有14%的人(7/50)惡化到2級以上,接受秋水仙鹼治療的群組有1.8%的人(1/55)症狀惡化到2級以上,危險對比值(Odds Ratio)[19]=0.11;95%信賴區間為0.01-0.96;P=0.02)。由於醫界已充分瞭解短期使用秋水仙鹼的安全性,為降低免疫風暴和心肌炎、心包炎所造成的影響,在開立皮質類固醇時連帶使用秋水仙鹼,會是種合理的選擇。
秋水仙鹼建議劑量:前3天0.6毫克,每日口服兩次,接下來30天劑量也是0.6毫克,但頻率改成每日口服一次。
點評
本篇論文〈免疫調節藥物〉的段落新增了布地奈德,其餘資訊可與前篇論文並參。
新冠肺炎多元藥物早期治療(四):抗血小板和抗血栓藥物
多項研究皆論述了感染新冠在病理學上會導致大型、微型血栓的比率增加。新冠患者產生胸悶的狀況與血氧濃度降低有關,而這個現象暗示著肺部可能出現血栓。多項研究表明新冠重症患者血液中的D-dimer量會增加,而這通常和患者的深層靜脈出現血栓、肺動脈出現栓塞有關。死亡病例經解剖後,有超過一半肺部皆出現微型血栓、明顯的栓塞和深層靜脈血栓。以上狀況都支持了一種假說,即某種特殊的血管內皮受損和血栓,在新冠患者血氧濃度下降中扮演要角,也是染疫患者之所以需要住院、接受支持照護(supportive care)的主要原因。由於染疫後人體內的血栓素A2會被顯著上調,建議要及早給病人每日服用劑量325毫克的阿斯匹林,達到初期的抗血小板和抗發炎效果。症狀較嚴重的非臥床病患也可接受皮下注射低分子量肝素,或像治療患有其他疾病的病患,開立口服新型抗血栓藥物。在一份涉及2773名新冠住院患者的回顧性研究中,有28%在為期兩天以內的住院期間接受了抗血栓療法治療,而儘管治療對象是症狀較重的患者,抗血栓療法仍與患者的死亡率下降有關,接受療程後的日均統計數據(per day of therapy)為:HR = 0.86,95%信賴區間為0.82-0.89;P<0.001。目前只有不到30%的住院病例有接受抗血栓療法治療。預防性質地使用低分子量肝素、新型抗血栓藥物治療新冠,與新冠死亡率下降超過50%有關。抗血栓藥物也可以降低血栓併發症、D-dimer上升,從而降低患有共病症的新冠患者死亡的機率。種種跡象也指示了症狀較重的非住院新冠病患也可採用預防性療法避免心因性血栓、靜脈栓塞。目前已經開展以非臥床病患為對象,使用阿斯匹林或新型口服抗血栓藥物治療的隨機實驗。然而,基於新冠症狀系統性地出現血栓,以及預防性、治療性抗血栓療法能使死亡率顯著下降等理由,給所有患有心、腎、惡性疾病的高風險新冠病患開立劑量325毫克的阿斯匹林,每日口服一次,預防血栓,是種審慎的選擇。
新冠肺炎早期治療 – 輸氧與看護
遠端看診可以初步評估新冠病患狀況,同時讓病患維持自主隔離。醫生藉由視訊、音訊問診,而體溫等重要資訊則由病患或家屬提供。居家病患健康管理的其中一個安全要素,是透過每日遠端診療,掌控居室空氣,或依醫囑使用製氧機,維持動脈血氧濃度,若有必要則需送院使用呼吸機供氧。若病人具備足夠醫療知識,則可在有良好看護的情況下俯臥協助呼吸。
本篇論文介紹的療法也適用於療養院或其他非醫療機構中感染新冠的高齡病患。除了開立口服藥,這些療養中心也可提供靜脈注射、單株抗體、輸氧等非口服用藥的療法,降低他們發展成重症而轉送醫療機構住院的風險。
結論
從人類生活遭受的影響程度而言,新冠肺炎這場瘟疫百年一遇。這場瘟疫其中一個特殊的地方,在於醫療監管機構並未以非住院病患為對象,從社區層面即時建立大型隨機臨床實驗。新冠肺炎與流感相似,病發之初會先經歷病毒複製的階段,而這個階段正是醫療措施介入的窗口,一個大大降低高風險病患產生嚴重後發症的機會。目前許多國家抱持新冠肺炎沒有抗病毒療法治療的觀念,採取觀望病情發展的醫療策略,放任病人症狀持續惡化。這無疑揮霍了治療新冠的寶貴時間,並且可能導致住院率、死亡率不必要地上升。一旦染疫,避免高風險病患住院的方式,是在症狀惡化到必須緊急送醫之前便予以治療。在政府並未支持針對普遍、平價、易取得的藥物進行隨機臨床實驗,以及針對非住院病患有指導性的醫療指南付之闕如的情況下,一線醫療人員必須根據臨床判斷,以及醫、病之間充分溝通的決策過程,予以早期治療。從臨床經驗、病理學、隨機臨床實驗數據、接受治療的自然史組而發展出來的「早期梯次性多元藥物療法」已經顯示了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對那些新確診且有出現症狀的高風險病患來說,梯次性多元藥物療法在產生療效的同時,也具有合理的損益比。直到本次疫情因群體免疫終結之前,在高風險非臥床病患染疫之初便及早使用梯次性多元藥物療法,應該成為治療新冠的標準程序。
本論文末尾註腳:為了瞭解諸國使用的早期治療藥物為何,論文作者查詢了巴西、秘魯、台灣、美國等國的政府官網,也在「PUBMED」資料庫查詢中國、法國、印度、南韓、非洲諸國的發表的研究報告,及從網路上的可靠渠道獲得了阿根廷、孟加拉、哥倫比亞、墨西哥、非洲諸國的相關資訊。
筆者註釋
[1] 醫學上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是指某種疾病在患病個體未接受治療的情況下的自然發展歷程。「接受治療的自然史」(treated natural history)指病人接受某種未明功效的療法後的疾病發展歷程。我在網路上沒查到「treated natural history」這個詞組,因此只能從《The treated natural history of high risk superficial bladder cancer: 15-year outcome》這篇論文推測其義。
[2] 「共病症」指病人除了正在接受治療的某種疾病外,還有其他已經存在,且會對這次的主診斷疾病產生影響的疾病。「併發症」則是指由某種疾病所引起的另一種疾病。「共病症」與「併發症」的區別,在於共病症之間並無因果關係,併發症反之。
[3] ACE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血管收縮素轉化酶2)是一種肺、動脈、心、腎、腸道等器官的組織細胞表面的膜蛋白。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可與ACE2結合,從而侵入人體細胞,因此是新冠病毒感染細胞的受體。
[4] 病毒蛋白酶在新冠病毒融入宿主細胞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也成了藥物治療的標靶。科學家力圖找出可以抑制病毒蛋白酶活性的抑制劑,從而阻斷病毒融入宿主細胞的過程。新冠病毒憑藉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與宿主細胞融合,刺突蛋白的形狀像是插在病毒表面的大頭針,結溝分成兩個部分,一是插著外殼的針,代號S2,二是針上的大頭,代號S1。刺突蛋白與宿主細胞結合時,針的大頭會和ACE2結合,結合後,弗林蛋白酶、TMPRSS2蛋白酶會共同切割S1、S2,使得S1從病毒表面脫落,露出的S2則會與宿主細胞膜融合。弗林蛋白酶切割 S1/S2 位點可能導致病毒 S 蛋白的 RBD 區域 和/或 S2 次單元發生結構改變。TMPRSS2 蛋白酶切割 S2′ 位點,被認為能夠促使病毒殼體宿主細胞融合。詳細資訊請參〈新冠病毒進入細胞的結構機制和功能機制〉。
[5] 白細胞介素-6是種多功能的細胞激素,可以調節抗體產量,和許多發炎性疾病的成因有關。
[6] 藥物上市後,按規定必須在廣告標籤上載明適應症。標籤外使用,即醫師將此藥用來治療廣告標籤上的載明的適應症以外的病症。一旦藥物成了老藥,它原來的廣告標籤就會有些不合時宜。據麥卡洛醫生的訪談,約有40%的藥品是在廣告標示的治療用途外使用的。「標籤外」用藥之所以是種必須,是因為新冠肺炎是2019年底才出現,把2019年以前上市的藥物用來治療新冠,都算是標籤外使用。
[7] 當細胞外的某個異物想進入細胞內時,首先要和細胞膜結合,被細胞包裹起來後,形成囊泡,稱之胞內體(endosome)。異物便藉由胞內體運輸進細胞內部。
[8] 「葡萄糖-六-磷酸鹽脫氫脢缺乏症」即蠶豆症,是種基因異常導致的先天性代謝疾病,「葡萄糖-六-磷酸鹽脫氫脢」是種可以協助葡萄糖新陳代謝的酵素,而在代謝過程中會產生一種保護紅血球的物質,從而對抗某些氧化物。缺乏這種酶,就會使紅血球容易受到某些特定物質的破壞而發生溶血,程度嚴重即發生「急性溶血性貧血」。
[9] 用藥後效力逐漸減弱,因而必須加大劑量,或增加服用頻率,稱之為藥物耐受性差;反之,若在較長時間內用藥,而藥效並未減弱,稱之為藥物耐受性好。
[10] 治療指數是指某種藥物能夠產生療效的劑量,與這個劑量所產生的毒性的比例。同樣劑量下,療效高,毒性低,便稱之為治療指數高,反之為治療指物低。
[11] 「RNA依賴性RNA聚合酶」是種以RNA為模板催化複製RNA的酶,簡稱RNA聚合酶。由於RNA聚合酶在新冠病毒的複製中扮演重大角色,許多藥物都以抑制RNA聚合酶為宗旨治療新冠肺炎。
[12] 網上搜到的選擇性/非選擇性抑制劑主要是以抗發炎藥為對象。比如阿斯匹林是種非選擇性抑制劑。COX-1、COX-2是一種酵素的兩種同質體,COX-1平時就存在於體內,COX-2則在身體發炎的時候會大量增加,服用阿斯匹林後可以同時抑制COX-1、COX-2,達到消炎的效果,但因COX-1可以促進「前列腺素」產生,而前列腺素可以可以減少胃酸分泌,增加胃粘膜的生成,因此阿斯匹林雖可透過抑制COX-2消炎,卻會同時因抑制COX-1而傷胃。若想消炎但又不想傷胃,便可使用抑制COX-2但不抑制COX-1的選擇性抑制劑。
[13] 風險比率的意義:分子是治療組,分母是沒用藥的控制組。假設在藥物實驗中,有用藥的群組死亡率是控制組的兩倍,則死亡風險比率為2,意味著用藥治療反而加劇死亡風險;風險比率<1,則意味著用實驗組所用之藥可以降低死亡風險。
[14] P值的意義:分母是實驗總次數,分子是實驗結果不符合假說的次數。假設羥氯喹能降低新冠肺炎死亡率,而藥物實驗總共進行了100次,有50次顯示羥氯奎無效,那麼P值=0.50,亦即羥氯喹與降低新冠肺炎無顯著關係。P<0.001意味著在一千次用羥氯喹治療新冠的藥物實驗中,只有不到一次產生風險比率上升的負面療效,統計學上稱之為顯著相關。簡言之,P值的意義是兩件事的關聯性是否強烈,無法表明是正面、負面關聯。
[15] 據《新冠肺炎早期門診治療的病理生理學基本原理》,單獨使用羥氯喹治療新冠病患的臨床實驗統計數據為:風險比率(Hazard Ratio)=0.34,95%信賴區間為0.25-0.46,P<0.001。使用羥氯喹+阿奇黴素的統計數據則為:風險比率=0.29,95%信賴區間為0.22-0.40,P<0.001。
[16] 白細胞介素-10是一種在免疫調節和發炎中具有多效性的細胞因子。 它下調了巨噬細胞上Th1細胞因子、MHC-II類抗原、共刺激分子的表現,並增強了B細胞的生存、增殖和產生抗體的能力。
[17] D-dimer是種纖維蛋白的代謝產物,在發生靜脈栓塞時會分解,因此血中濃度便會提升。D-dimer上升意味著血管可能有栓塞的情形。
[18] 0級為未感染。1級為有感染但症狀輕微,活動能力並未受限。2級為症狀加劇使活動能力受限。最嚴重則是死亡,為8級。參下表:

[19] 危險對比值,在病歷對照研究中的定義是「實驗組中發生疾病的機率/控制組中發生疾病的機率」,在本實驗中,即1.8%/14%約等於0.13,不是0.11。可能實驗數據有引入其他算法,或者數字誤植。
附錄
附錄一:各國使用的新冠肺炎早期治療藥物,台灣也名列其中。

附錄二:新冠肺炎病情發展圖,橫軸為病情發展天數,縱軸為死亡風險,黃、藍、紅方塊依序是「病毒複製」、「免疫風暴」、「血栓」。

附錄三:新冠肺炎多元藥物早期治療流程圖,與前篇論文大同小異。